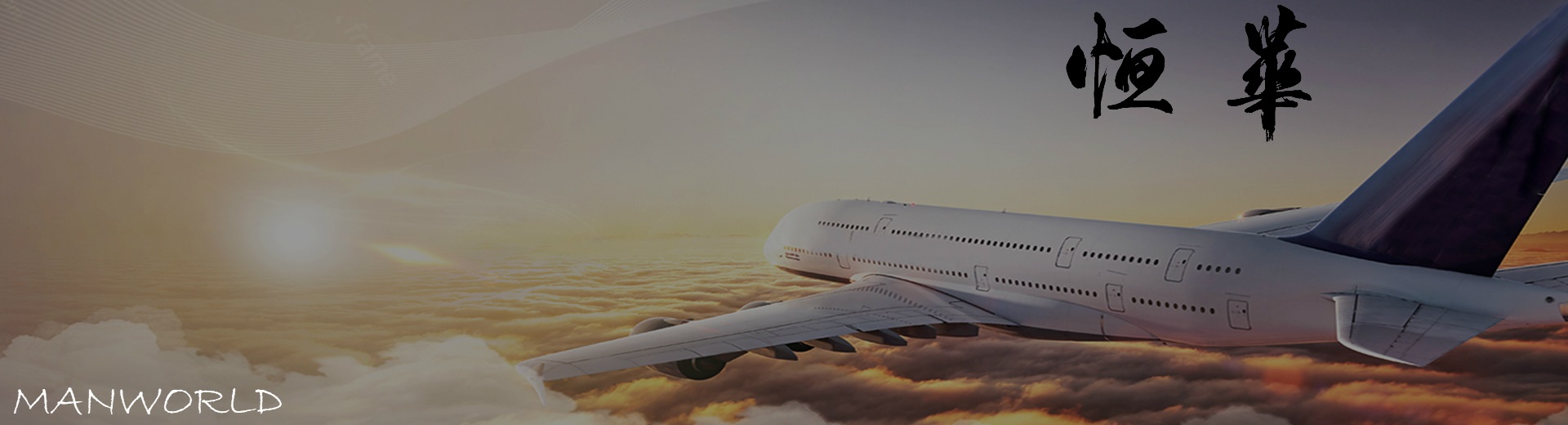:船舶碰撞案件的专业化程度大多数表现在船舶过失程度的认定,不仅涉及船舶知识,还涉及航行规则的违反程度,以及对事故发生的因果关系,最能体现海事审判专业化水平。一般的海事法官而言,由于知识结构,对航行规则的不熟悉,较难确定碰撞双方违反航行规则情况,对双方的过失程度判断比较吃力,特别是在缺少海事报告的情况下。笔者主要根据广州海事法院20年船舶碰撞案件判决认定情况,力争总结出认定过错程度的一般规律,供各方海事从业者参考,以期达到当事人快速解决纠纷、服务于航运业的高水平发展之目的。
归责,是指行为人因其行为和物件致他人损害的事实发生以后,应依何种根据使其负责。此种依据体现了法律的价值判断,即法律应以行为人的过错还是应以已发生的损害结果为价值判断标准,抑或以公平考虑等作为价值判断标准,而使行为人承担相应的责任。[1]船舶碰撞产生的民事责任如何归责?船舶碰撞本质上属于民事侵权的一种,归责原则整体上适用一般民事侵权的归责原则,只有在海商法等特别法有规定时才适用特殊的归责原则。由于我国没有涉及内河船舶碰撞的特别法,因此内河船舶的碰撞适用一般民事侵权的法律规定。
故意碰撞在司法实践中极少见,《海商法》和船舶碰撞司法解释均没有专门规定,应适用一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四条之规定,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相应的责任。对于故意碰撞方自己遭受的损失,因其过错严重,应承担全部责任。故意碰撞涉及故意损害他人财产或人身的,还应根据行政法和刑法承担对应的行政和刑事责任,本文不作展开。
《海商法》第一百六十七条规定,船舶发生碰撞,是由于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能归责于任何一方的原因或没办法查明的问题导致的,碰撞各方互相不负赔偿责任。
根据过错责任归责原则,行为人只对自己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不可抗力属于不可预见、不可避免并不能克服的事故[2],让行为人承担相应的责任没有法理和价值上的正当性。
涉台风的碰撞事故船方是否可免责?对此应用与时俱进的眼光去看,以前由于科学技术手段的落后,台风的可预见性很差,因此对于比较大的台风,只要船方在可避免和克服方面做的没什么失职,一般认定为不可抗力造成可以免责。如今所处信息时代,气象卫星和云图等手段预报天气已经很普遍,台风的路径很早就能被预测,根据海事审判实践,对于一般的台风,船方不能以不可抗力免责,但是对于个别特殊的台风,特别是与预报路径和强度发生较大变化的,如果船方在防台方面无过错,通常能不可抗力免责。
(1) 不能免责的情形。广州海事法院审理的“顺宏海1188”轮案[3]。一审认为,因气象预报部门对“天鸽”台风登陆的大致时间、区域等信息均已提前发布预报和公告,虽然“天鸽”台风的风力强度、路径、伴随的风暴潮等情形超出了气象预报的范围,海事部门经调查后认定船舶对台风影响估计不足,采取一定的措施不足,故船方对防台有过失,应承担对应责任。二审维持一审判决。
(2)可免责的情形。广州海事法院“南鸿918”轮案,一审认为,涉案碰撞事故是由于“南鸿918”轮因台风走锚碰撞到锚泊的“恒惟星”轮,“恒惟星”轮作为一艘无动力工程船,在港内锚泊抗台,在事故发生时没发生移动、走锚,对碰撞的发生没有责任。“南鸿918”轮走锚是导致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水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恶劣天气海况是造成本次事故发生的原因,但并未从不可抗力构成的三个要件出发对本次台风是否构成不可抗力进行法律上的分析。该责任认定书仅写明台风正面袭击湛江港以及台风的强度,东某公司还需进一步证明台风的强度、影响区域已超出天气预报的强度和范围,进而构成不可预见;其次,由于船舶属于可移动工具,东某公司应验证自己在台风前、台风中采取了适当且合理的抗台风措施。东某公司并未提供证据证明其采取了何种避风措施,应对“南鸿918”轮走锚碰撞恒某公司所属的“恒惟星”轮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二审认为,恒某公司主张东某公司就涉案碰撞事故承担侵权责任,应举证证明东某公司就该事故的发生负有过错。在查明“南鸿918”轮为避免事故发生所采取相关措施的基础上,恒某公司提出东某公司在防抗台风时存在不合理之处,因事故发生时“南鸿918”轮尚在申办有关证照,其并无最低安全配员要求,且未正式投入营运。故在台风到来前要求东某公司安排对该轮有着非常丰富实践操作经验的船员防抗台风,不具备现实条件。东某公司在获知台风预报信息后,已安排“南鸿918”前往锚地避台,并采取抛一字型锚和打压载水等措施。涉案事故发生时,台风风力达到15级以上、阵风超过17级,瞬时风速达到67.2米/秒,可见其风力已明显超出了原预见范围。“南鸿918”轮采取的防抗台风措施,与当事人在事故发生前能预见到的风险程度基本相称。海事部门出示的《水上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和事故调查报告,亦认定该事故属于台风风灾事故,并未指出东某公司对此负责任。现恒某公司不能举证证明东某公司存在过错,应当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审查后,驳回恒某公司的再审申请。[4]
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此类型事故越来越罕见,暂未发现此类案例。此类案例如果有,一般发生在大洋上,且事故船均已沉没无法打捞,人员亦全部身亡。否则按照现代科学技术手段,一般能调查出事故大概经过,也能确定双方的主次责任。
过失是指行为人并不存在希望损害发生的意图,但对损害的发生应该能够预见但却没有预见,致使损害发生。在海商法中,通常所说的过失是指行为人具有过失心理健康状态且据此作出的行为,即过失行为,而不是单指过失的心理健康状态[5]。判断是否构成过失有两种依据,一种是以当事人能否预见到为标准,即主观标准,由于每个人的知识能力不同,该标准会因人而异。另外一种是以当事人应该能预见到为标准,即一般人的能力为判断标准,不以单个人的自身能力为标准,即客观标准,该标准比较好掌握。按照我国法律和法规规定,船员需经过专业学习和培训,通过适任考试后取得相应的资质,即一名持证船员应该拥有相对应的航海能力。拥有相对应航海能力的船员,如果严格按照规则行事,碰撞事故通常能避免。故船舶碰撞事故中的过失,应以通常船员所具有的能力作为判断标准,即以客观标准为主,结合主观心态作出判断。碰撞事故中的过失判定主要是根据避碰规则、人员适任、船舶适航性、避碰规则的遵守等。
《海商法》第一百六十八条规定,船舶发生碰撞,是由于一船的过失造成的,由有过失的船舶负赔偿相应的责任。此种情形一般发生在航船碰撞锚泊船或者靠泊船,在航船之间碰撞承担单方责任较少。
在航船碰撞靠泊船,一般由在航船承担全部责任。广州海事法院审理的“金泰7”轮碰撞案[6]。该轮未仔细地了解船舶掉头水域情况及探测附近船舶位置和动态,对船舶掉头操纵存在的困难估计不足,应急措施准备不足,在船舶出现碰撞危险时未能及时果断下令抛锚。“金泰7”轮掉头时,应使用一切有效的手段充分估计到碰撞危险和别的可能危害航行安全的局面,值班驾驶员须充分掌握在任何吃水情况下本船的冲程等操纵特性及其设备操作上的局限性。“金泰7”轮船长在掉头操纵船舶过程中未采用安全航速。“宝晖”轮停靠码头,没有证据证明其存在过失。“金泰7”轮承担100%的过失责任。
广州海事法院审理的“金辉568”轮碰撞案[7]。中国船级社广州分社向原告签发内河浮船坞安全证书,认定“千山”号浮坞船体结构与强度、排水设施、电气装置、消防符合标准要求,该浮坞处于安全作业状态,准予在广州港区作业。被告所属“金辉568”轮自香港出发开往佛山新港。该轮航经“千山”号浮坞附近时船舵失灵,撞向浮坞导致后者发生损毁。该轮船舵失灵而撞向“千山”号浮坞,导致浮坞受损,应承担全部责任。
青岛海事法院审理的“鲁日海渔60319”碰撞案[8]。“鲁岚渔61372”渔船在113海区锚泊期间,被航行中的“鲁日海渔60319”渔船碰撞。法院认定,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鲁日海渔60319”渔船驾驶人员在驾驶操作中睡觉导致碰撞事故,航行中没有值班瞭望人员,“鲁日海渔60319”渔船对本次碰撞事故承担全部责任;“鲁岚渔61372”渔船是锚泊船,号灯显示正确,在碰撞前采取了声号及雾灯提示措施得当,在本次事故中不承担责任。
广州海事法院审理的“昌达12”轮碰撞案[9]。“昌达12”轮在高栏港锚地锚泊时受寒潮大风影响走锚碰撞锚泊船“保得1132”轮。“昌达12”轮配员严重不足,仅2名水手在船值班,船长、轮机长等高级船员均离船,值班水手安全意识薄弱,低估了冬季寒潮大风对锚泊船安全的影响,没有在恶劣天气来临时加强值班和瞭望,发现船舶走锚后没能力操纵船舶,未采取比较有效的措施抗风避碰。“保得1132”轮在锚泊中发现“昌达12”轮走锚后,立即备车、通过VHF呼叫对方船并准备碰垫,尽可能地采取避碰措施进行避让。“昌达12”轮配员严重不足,走锚时值班船员正在厨房做饭,没有瞭望,走锚后未采取比较有效措施制止走锚或进行避让,负全部责任。
互有过失的船舶碰撞情形发生在航船之间最多,主要存在的过失为值班人员不适任,瞭望疏忽、没有采用安全航速,让路船没有按“早大宽清”原则采取避让措施,直航船在紧迫局面时没有及时果断采取避让措施等等。
广州海事法院审理的“利通88”轮碰撞案[10]。事故发生前,“利通88”轮一直占用进港航道航行,与“江苏三航6”轮形成碰撞紧迫局面并最后导致碰撞事故的发生,违反了《珠江口水域船舶安全航行规定》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利通88”轮疏忽瞭望,没有在航行中充分的利用一切手段保持正规瞭望及早发现来船,违反了《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五条的规定。在两船存在碰撞危险,双方在确定左舷对左舷会船后,“利通88”轮只是先用小幅度向右转向,直到两轮相距不足400米时才用右满舵大幅度向右转向,船舶转向不及时最后导致两船碰撞发生,违反了《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八条的规定。“江苏三航6”轮没用安全航速,在碰撞危险局面已形成时,没有及时降速行驶,造成碰撞事故不可避免,违反《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六条的规定。“江苏三航6”轮没有对碰撞危险局面作出充分估计,及时采取比较有效避碰措施,在VHF呼叫、闪绿灯未获对方回应的情况下,未引起足够的警觉并采取对应的避让行动,仍然保向保速航行,在两轮相距400米时才采取停车、倒车操作,违反了《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八条的规定。“利通88”轮和“江苏三航6”轮上述过失均是导致本案船舶碰撞事故发生的原因。法院判定,“利通88”轮承担60%的过失责任,“江苏三航6”轮承担40%的过失责任。
广州海事法院审理的“亚洲香港26”轮案[11]。事故水域能见度良好,初见时处于交叉相遇局面,“亚洲香港26”轮属于让路船,“宏浦35”轮属于直航船。“亚洲香港26”轮没有保持正规瞭望,未正确使用雷达进行远距离扫描,违反《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五条和第七条的规定;作为让路船,在两船已构成紧迫局面的情况下,才采取大幅右舵的措施,违反《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十六条的规定,是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宏浦35”轮船长在能见度良好的情况下,在两船相距仅1海里时才发现来船,没有保持正规瞭望,违反了《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五条的规定;作为直航船,在发现来船迟迟不采取行动后,直至两船相距0.4海里时才采取避让行动,违反了《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法院认定“宏浦35”轮承担30%的过失责任,“亚洲香港26”轮承担70%的过失责任。
广州海事法院审理的“瑞达9”轮碰撞案[12]。“瑞达9”轮航海日志记载,该轮碰撞前发现“粤清远货2979”轮后采取减速及右舵5°向右转向,该记载与广州沙角海事处提供的调查询问笔录和原告向广州沙角海事处提供的水上交通事故报告书的记载一致,但与“瑞达9”轮提交的海上交通事故报告书中的记载相矛盾。此外,广州沙角海事处事故后向两船船员做的水上交通事故调查询问笔录和两船向广州沙角海事处提交的水上交通事故报告书显示,双方对初见时各自船位、相互距离、灯号状况,紧迫局面的形成过程和最终事故位置的表述均无法相互印证,致使法院对两船过失程度没办法判定,依照《海商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款认定,两船平均承担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第31号指导性案例。航行过程中,当事船舶协商不以《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确立的规则交会,发生碰撞事故后,双方约定的内容以及当事船舶在发生碰撞事故时违反约定的情形,不应作为人民法院判定双方责任的依据,仍应当以前述规则为准据,在综合分析紧迫局面形成原因、当事船舶双方过错程度及处置措施恰当与否的基础上,对事故责任作出认定。在两轮达成一致意见前,两轮交叉相遇时,本应“红灯交会”。“玫瑰”轮提议“绿灯交会”,该提议违背了《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规定的其应承担的让路义务,但“炜伦06”轮同意该提议。此时,双方绿灯交会的意向应是指在整个避让过程中,双方都应始终向对方显示本船的绿灯舷侧。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没有《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意义上的“让路船”和“直航船”。因此,当两轮发生碰撞危险时,两轮应具有同等的避免碰撞的责任,两轮均应按照《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的相关规定,特别谨慎驾驶。在达成绿灯交会的一致意向后,双方都认为对方会给自己让路,未能对所处水域的情况做有效观察并对当时的局面和碰撞危险作出充分估计,直至紧迫危险形成后才采取行动,最终没办法避免碰撞。综上,两轮均有瞭望疏忽、未使用安全航速、未能尽到特别谨慎驾驶的义务并尽早采取避免碰撞的行为,对碰撞事故的发生责任相当,应各承担50%的责任。
对于船舶避让措施的过失,涉及航行规则的适用,如港章、地方规则、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的适用,很复杂,另外还涉及船舶之间航路权优先等级的关系。在能见度良好的情况下,失控船、操纵能力受限的船舶航路权等级最高,其他机动船都要给它让路;其次是从事捕鱼的船舶,其他机动船要给它让路。如果能见度不良,就没有让路船与直航船的区分,各船都需最大谨慎航行,采取一切措施避免碰撞,不会有一船专门给另一船让路的情形,因为在能见度不良的情况下,互相无法用肉眼看清对方态势,不能形成互见,只能靠大家都谨慎慢行以避免碰撞事故发生。
一般的船舶碰撞事故都有此项过失,此项过失一般为重过失,对责任承担有较大影响。《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五条规定,每一船舶应常常使用视觉、听觉以及适合当时环境和情况下一切有效的手段保持正规的瞭望,以便对局面和碰撞危险作出充分的估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避碰规则》第六条规定,船舶应当随时用视觉、听觉以及一切有效手段保持正规瞭望,随时注意周围环境和来船状态,以便对局面和碰撞危险作出充分的估计。前述规则均在非常靠前的条文规定瞭望,可见保持正规瞭望对一船的重要性。
船舶碰撞事故统计根据结果得出,没有保持正规瞭望甚至无人瞭望,是绝大多数碰撞事故发生的原因。瞭望通常意指“对船舶所处水域的一切情况做观察,并对发生的一切情况作出充分的估计和分析”[13]。瞭望的目的不仅在于观察,更在于分析和判断。从规则行文看,瞭望条款是适用于任何一个时间里、任何船舶,包括在航船、锚泊船,即使是失去控制的船舶和操纵能力受限等享有最高航路权的船舶,仍应保持正规瞭望,否则将会被指责有过失,从而判定责任。
瞭望人员是指专门负责或承担对周围的海况做全面观察的航行人员。1978年STCW公约第二章“航行值班中应遵守的根本原则”第9条规定:为保持正规瞭望,瞭望人员应集中精力,并不应承担或者分配给会妨碍本工作的其他任务,瞭望人员和舵工的职责是分开的,舵工在操舵时不应被视为瞭望人员,但在小船上,能在操舵位置无阻碍地看到周围情况,且不存在夜间视力减损或执行正规瞭望的其他障碍除外。
瞭望人员应具备如下条件,一是具备履行瞭望职责的体质,如视力不能有色盲;二是需要具备一定的航海知识,掌握一定的航海技能。除非另有充分证据,只有具备一级水手或者三副以上适任证书的,才可视为具备瞭望资质。至于瞭望的手段,并不是通常理解的视觉观测,而是包括视觉、听觉以及适合当时环境下的一切手段。听觉主要是用来获取船舶声号方面的信息,特别是能见度不良,如《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四章专门对各种情形下船舶应使用的声号作出了规定,如其中的第三十五条规定了在能见度不良的情形下各种船舶使用的声号。由于能见度不良,视觉瞭望严重受限,声号的获取及听觉瞭望对于船舶安全航行很重要,当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雷达等现代化助航设备的作用逐渐重要,但是无论如何不能代替听觉的瞭望。其他的瞭望手段还包括雷达、自动标绘雷达的值守,VHF的值守等。
保持正规瞭望不仅是在航船的责任,也是锚泊船的责任,锚泊船如有违反也应承担对应的责任。广州海事法院审理的 “顺晖610”轮案[14]。“顺晖610”轮疏忽瞭望,锚泊船“粤湛渔01103”船未安排人员锚泊值班、疏忽瞭望。作为在航船的“顺晖610”轮疏忽瞭望,未曾发现锚泊的“粤湛渔01103”船,以致没有采取任何避让措施,是碰撞发生的根本原因。“顺晖610”轮承担75%的过失责任,“粤湛渔01103”船承担25%的过失责任。
此过失对事故发生有重要影响,在判定责任中是一个重要考虑因素。安全航速是指凡是能采取适当有效的避碰行动,并能在适合当时环境和情况的距离以内把船停住的速度。[15]到底多少节为安全航速,《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没有作规定,也无法作明确规定,因为这与当时的航行环境紧密关联。如果当地航行规则有限速规定,超过最高限速肯定不是安全航速,低于限速也并不全是安全航速,特别是航速太低会导致船舶无法保持舵效,极度影响船舶操纵。
广州海事法院“繁安69”轮碰撞案[16]。事故发生水域当时处于防台风预警状态下,“繁安69”轮本应该判断到河道中有众多锚泊避风的船舶,并应采取减速航行,加强瞭望,谨慎驾驶的措施。但当班驾驶员疏忽瞭望,未采取安全航速航行,当距他船约350米时才发现对方船舶,驾驶员虽采取全速倒车、操右满舵的紧急措施,但都为时过晚,与对方船发生了碰撞。该船在疏忽瞭望、判断碰撞危险、采取避碰措施方面存在严重过失,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避碰规则》第六条、第七条、第九条第一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繁安69”轮没有尽可能沿本船右舷一侧航道行驶是导致事故的重要原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避碰规则》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十六条规定。“繁安69”轮船员配备不足,时值台风吹袭期间,没有配备持有适任证书的水手和GMDSS操作员加强值班瞭望,也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粤惠州货0326”轮在避台锚泊期间,没有开启雷达、甚高频无线电话以及AIS设备,值班船长直到他船距离本船大约80米处才发现有船驶来,没有随时用一切有效的手段保持正规的瞭望,存在疏忽瞭望的过失,违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避碰规则》第六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在防台风特别时段,“粤惠州货0326”轮未留有足以保证船舶安全的船员值班,未采取加强值班的措施,也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之一。“繁安69”轮承担80%的责任,“粤惠州货0326”轮承担20%的责任。
对遇是指两艘机动船在相反或接近相反的航向上相遇致有构成碰撞危险。根据《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十四条规定,双方均应向右转向,从而各从他船的左舷驶过。未按规定及时采取避让措施的船舶一般承担主要责任。
广州海事法院审理的“铭扬洲179”轮碰撞案[17]。“铭扬洲179”轮在“穗东方332”轮右舷舷角6°方位,两轮形成对遇局面。在两轮相距约1000米构成对遇局面时,“穗东方332”轮没有利用一切有效手段及早发现来船并采取比较有效措施避免碰撞,在两轮相距约500米时才发现“铭扬洲179”轮,此时两轮已形成碰撞危险紧迫局面。两轮形成碰撞危险对遇局面,在“铭扬洲179”轮要求会红灯的情况下,“穗东方332”轮没有对会遇局面作出正确的判断,仍然认为应绿灯会遇,并向左转向,导致碰撞事故的发生,违反了《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十四条的规定。“铭扬洲179”轮在两轮相距约1000米形成对遇局面、构成碰撞危险时,未重视来船的航行动态,在发现来船要求绿灯会船及避让行动异常的情况下,未能及早采取比较有效措施,包括减速、停车、倒车或大幅度的转向以及别的可能背离规则的有效措施,以避免碰撞,违反了《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八条的规定。“穗东方332”轮在两轮处于对遇紧迫局面的情况下,错误地采取向左转向的避让行动,是碰撞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穗东方332”轮承担70%的责任,“铭扬洲179”轮承担30%的责任。
根据《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追越是一船从他船正横后大于22.5度的某一方向赶上他船时,即该船对其所追越的船所处的位置,在夜间只能看到被追越船的尾灯而不能看见它的任一舷灯。构成追越的条件具体是:1.追越船所处的方位为被追越船正横后大于22.5度角;2.追越船与被追越船处于互见中;3.追越船的船速大于被追越船。由于航海上的谨慎性和避免碰撞的需要,《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当一船对其是否在追越他船存有任何怀疑时,应假定在追越并应采取对应的行动。为避免追越船与被追越船方位的变化导致避让权利义务混乱,该条第四款规定,随后两船的方位的任何变化,并不能改变追越船和被追越船的权利义务,直到追越船驶过让清为止。我国《内河避碰规则》对于内河追越也有类似规定。通常情况下,追越船因违反相关规则而判定承担主要责任甚至全部责任。
广州海事法院审理的“顺利77”轮碰撞案[18]。“顺利77”轮由三水开往顺德途经顺德水道大洲监管点对开水域时,在追越“桂平南货3933”轮的过程中发生碰撞事故,“顺利77”轮在本次碰撞事故中负全部责任。
交叉相遇,指两机动船船艏相交叉,但不包括对遇局面和追越局面。一般由首先违反避让规则导致碰撞危险方承担主责。根据《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十五条规定,有他船在本船右舷的船舶应该给他船让路。进入互见状态后,应及时判断会遇态势,决定谁是直航船谁是让路船。让路船不让路导致碰撞紧迫局面的出现,往往负有较大责任。
最典型的案例是东某公司与北某公司等船舶碰撞损害赔偿纠纷案,该案历经一、二审均认为直航船独采取避让措施不当是主要过失,应承担主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提审后认为,让路船不及时采取避让措施是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应承担主要责任,直航船独自采取一定的措施不当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承担次要责任[19]。具体如下:
一审认为:“东方海外欧洲”轮与“兴海668”轮形成交叉相遇格局,“兴海668”轮为让路船。“兴海668”轮应及早减慢速度,并采取大幅度向右转向以避让直航船,但是,“兴海668”轮迟延采取一定的措施,是造成本案碰撞危险局面的原因之一。“东方海外欧洲”轮为直航船,负有保向保速义务。“东方海外欧洲”轮应沿着东博寮水道出口分道,驶向担杆水道出口分道,再向左转向。但是,“东方海外欧洲”轮未采取一切有效手段保持瞭望,并作出合理判断,刚进入东博寮水道分道通航制区端部警戒区时即开始大幅度左转,造成两船紧迫局面。“东方海外欧洲”轮称,由于“兴海668”轮未及时采取右转避让措施,其被迫根据《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十七条第1款第(2)项的规定,独自采取操纵行动,以避免碰撞。但根据《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十七条第1款第(3)项的规定,即使“兴海668”轮未及早让路,在当时的环境下,“东方海外欧洲”轮独自采取行动也不应对在本船左舷的“兴海668”轮采取向左转向。并且,“东方海外欧洲”轮在发现“兴海668”轮已经向右转向避让的情况下,仍继续大幅度左转。“东方海外欧洲”轮的错误行动是导致本案碰撞危险局面的根本原因。“东方海外欧洲”轮承担60%责任,“兴海668”轮承担40%责任。二审维持一审法院的责任判定。
最高人民法院提审认为,“东方海外欧洲”轮与“兴海668”轮形成交叉相遇的局面。在交叉相遇的局面下,相对直航船而言,让路船具有更大的避碰义务。让路船没有及早履行让路义务,导致紧迫局面形成的,应当对碰撞事故承担主要责任。因“东方海外欧洲”轮在“兴海668”轮右舷,故“东方海外欧洲”轮为直航船,“兴海668”轮为让路船。“兴海668”轮应当尽早采取行动,给“东方海外欧洲”轮让路。在初见后6分钟里,“兴海668轮”始终没采取任何行动,直至碰撞事故发生前2分钟才开始向右转向,违反了《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八条、第十五条和第十六条的规定,导致两船形成紧迫局面,应当承担碰撞事故的主要责任。“东方海外欧洲”轮作为直航船应保持航向和航速,当让路船“兴海668”轮没有采取适当行动履行让路义务时,“东方海外欧洲”轮可以独自采取操纵行动,以避免碰撞。依照《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十七条第3项的规定,在交叉相遇局面下,直航船采取避碰行为时,当时环境许可,不应对在本船左舷的船采取向左转向。本案中,“兴海668”轮没有及时让路,导致两船形成紧迫局面后,“东方海外欧洲”轮采取避碰行动时突然向左大幅转向,违反了《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十七条第3项的规定,也是导致碰撞事故发生的重要原因。“兴海668”轮应对碰撞事故承担60%的责任,“东方海外欧洲”轮应承担40%的责任。
根据《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规定,除了遵守第二章第一节的行动规则,即保持正规瞭望,使用安全航速等外,还应该遵守第三节船舶在能见度不良的特殊规定,即船舶保持随时操纵的准备,开启雷达(如有)及早判断是不是真的存在碰撞危险并采取避让行动,听到他船雾号时需减速谨慎驾驶。
广州海事法院审理的“三井策略”轮碰撞案[20]。“三井策略”轮至碰撞发生前20秒,始终使用自动舵,保持17.5节左右航速。作为一艘近8万总吨的重载集装箱船,在交通繁忙、渔船众多、通航环境复杂的南北航线上,尤其是在能见度不良、视线极差的情况下,仍然以如此高速行驶,且未将机器做好随时操纵的准备,违反《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六条和第九条规定,是导致事故发生的根本原因。“三井策略”轮在进入能见度不良水域后,驾驶台两侧舱门长期处在关闭状态,违反《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五条的规定。“三井策略”轮在雷达发现他船后,未有效使用获得碰撞危险的早期警报,违反《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七条和第十九条规定。“珍河”轮碰撞前属于“在航,不对水移动”,根据《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应以每次不超过2分钟的间隔连续鸣放二长声,但“珍河”一直未鸣放雾号。“珍河”轮在事发前已经备车,做好了随时操纵的准备,且已通过瞭望发现了“三井策略”轮并了解其动态,但大副一直未及早采取避让措施,是导致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三井策略”轮承担80%的责任,“珍河”轮承担20%的责任。
未保持在航道的右侧航行,占用对方船航道,致碰撞危险发生,一般应承担主要责任。《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九条第一项规定:船舶沿狭水道或航道行驶时,只要安全可行,应尽量靠近本船右舷的该水道或航道的外缘行驶。在分道通航的地方规定里,也有类似规定。
广州海事法院“振洋海1”轮碰撞案[21]。“振洋海1”轮在广州港伶仃航道的进港航道上航行,“江夏锦”轮在出港航道上航行,按照《珠江口水域船舶安全航行规定》第六条的规定,尽量靠近本船右舷的航道外缘行驶。“江夏锦”轮靠近本船左舷一侧的航道航行,违反《珠江口水域船舶安全航行规定》第六条的规定。《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十四条规定,当两艘机动船在相反的或接近相反的航向上相遇致有构成碰撞危险时,各应向右转向,从而各从他船的左舷驶过。“江夏锦”轮在看到“振洋海1”轮有大幅度向左转向的时候,再次向左转向,违反了《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十四条的规定。“振洋海1”轮发现“江夏锦”轮航行在进港航道后,船长未下令减速,在碰撞时两船之间的相对运动速度较大,导致损害严重。“振洋海1”轮在事故发生前未及时减速,违反了《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六条关于安全航速的规定。“振洋海1”轮有大幅度向左转向,违反了《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十四条的规定。“江夏锦”轮航行至靠近本船左舷的航道一侧、“振洋海1”轮未及时减速以及两船在事故前向左转向,是事故的直接原因。由于“江夏锦”轮航行至靠近本船左舷的航道一侧的行为,导致了两船之间出现碰撞危险,其过失程度大于“振洋海1”轮。法院判定“江夏锦”轮承担70%的过失责任,“振洋海1”轮承担30%的过失责任。二审维持一审的判定。
没有按照最低配员证书配备人员,常出现的是人员缺少,人员与最低配员证书要求不符,船员类型与船舶类型不符,如无线航区的船舶持配备沿海航区的证书的船员。当然在以人员配置问题确定船舶避让的过失时,要注意需有因果关系,如机舱配备缺少一个机工,与驾驶人员操作失误致使船舶碰撞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一般不作为确定过失责任比例的因素。
广州海事法院审理的“锦航18”轮案[22]。事发时能见度良好,“鲁荣渔52311”向西南方向航行,为让路船;“锦航18”轮位于“鲁荣渔52311”右舷向南航行,为直航船。“鲁荣渔52311”轮两名驾驶台值班人员均未持有有效的渔业船舶船员适任证书,违反《山东省渔业港口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的规定,不能够满足航行安全要求;负责瞭望的水手却在修理罗经照明灯,负责操舵的水手的视线被挡住,再加上驾驶台前窗玻璃视线不佳,未能保持正规瞭望,致使其不能及时有效地发现前方交叉航行的“锦航18”轮,违反《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五条的规定;该轮作为让路船,没有履行让路船职责,违反《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十六条规定。“锦航18”轮作为直航船,在发现“鲁荣渔52311”轮与本船业已形成紧迫局面时,未能及时采取比较有效措施避免碰撞,违反《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十七条第二款、第三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法院判定,“鲁荣渔52311”轮承担80%的责任,“锦航18”轮承担20%的责任。
该类问题有助航设施配备不全,船舶主机、舵机出现一些明显的异常问题,关闭AIS系统,号灯开启不当或有故障,号型悬挂不当等。当然,过失须与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才能作为过错程度的考量因素。如一船晚上抛锚,开启了锚灯,但锚灯使用了普通的照明灯泡,没用船舶专用的灯泡,这对事故的发生有因果关系,作为判定锚泊船过错程度的一个因素。
多船碰撞事故的情形很复杂,避碰规则规定的会遇态势一般是针对两船,在三船以上的碰撞中不能适用,只能根据避碰规则的一般条款判定各船过失,如《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二章第一节、第三节,第二节不能适用,而遵循的原则是由首先违反避碰规则导致碰撞危险产生的船舶承担主责,其他船舶根据其过失程度与碰撞事故的关联性分别确定责任,如下述案例是因“翔富8”轮使用主航道时未尽量靠近其右舷的该航道的外缘行驶,相反,其沿航道左侧航行,违反了《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九条第一款和《珠江口水域船舶安全航行规定》第六条第一款规定,导致碰撞危险发生,应承担主要责任。
广州海事法院“翔富8”轮碰撞案[24]。作为出口船舶的“恒晖15”轮驶过52号灯浮时,注意到前方有三艘进口船舶,即“东方223”轮在航道外西侧航行,“翔富8”轮沿航道西侧边线”在航道内航行。“恒晖15”轮呼叫了“翔富8”轮,但未得到回复,便通过打激光灯闪红灯方式希望能与“翔富8”轮会红灯,但“翔富8”轮未回应,只是向左调整航向计划驶出航道。在未进行连续观测和标绘的情况下,“恒晖15”轮独自采取向右转向的措施,调整航向正对着50号灯浮航行。调整航向后,仍未核实“翔富8”轮和“东方223”轮的航行态势,继续采取向右转向措施,导致与“东方223”轮产生紧迫局面。“恒晖15”轮疏忽瞭望,违反了《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五条的规定。“恒晖15”轮航速从始至终保持在11节左右,碰撞前11秒时的速度为8.7节。“恒晖15”轮在前方有多艘船舶同时进口,且对每艘船舶的动态不明了的情况下,未采取比较有效的减速措施,其未使用安全航速,违反了《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六条的规定。在距“翔富8”轮约0.7海里、距离“广州发展2”轮1.4海里时,“恒晖15”轮右舵10度向右转向,计划从“翔富8”轮左侧通过,此行动直接造成该轮分别与“东方223”轮、“翔富8”轮形成碰撞紧迫局面。距离“东方223”轮约0.2海里时,“恒晖15”轮发现“翔富8”轮向左转向,于是采取紧急停车、继续大幅度向右转向,从而与“东方223”轮造成碰撞。“恒晖15”轮避免碰撞的行动和措施不当,违反了《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八条第一款、第三款和第四款的规定。
“东方223”轮在沿航道西侧航行至48号灯浮时,已经注意到正前方来船“恒晖15”轮和右后方来船“翔富8”轮,本有足够时间对局面和碰撞危险作出充分估计,但在发现“恒晖15”轮小角度向右调整航向时,想当然地认为其还会转回航道,未能观察到“恒晖15”轮向右转向是为了避让右后侧的追越船“翔富8”轮。“东方223”轮疏忽瞭望,违反了《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五条的规定。“东方223”轮在发现“恒晖15”轮小角度向右转向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缺乏应有的戒备,继续保向保速行驶,直至碰撞不可避免时才减速、倒车。“东方223”轮没有对碰撞危险作出充分估计和判断,违反了《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七条第一款的规定。
“翔富8”轮作为进口船舶,使用主航道时未尽量靠近其右舷的该航道的外缘行驶,相反,其沿航道左侧航行,违反了《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九条第一款和《珠江口水域船舶安全航行规定》第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在碰撞事故发生前,“翔富8”轮沿航道左侧航行,直接影响了“恒晖15”轮后续采取的避让措施。“翔富8”轮在航经50号灯浮时观察到“恒晖15”轮小角度向右转向,“翔富8”轮在距离“恒晖15”轮约0.7海里时,采取向左转向的措施往主航道外行驶,后因“恒晖15”轮大幅度右转与“东方223”轮发生碰撞,“翔富8”轮立即采取了大幅度右转措施避免了碰撞。在此过程中,“翔富8”轮妨碍主航道其他船舶的正常航行,违反了《珠江口水域船舶安全航行规定》第六条第一款和第四款的规定。“翔富8”轮在采取向左转向之前航向约345度,“恒晖15”轮航向约167度,两船在接近相反航向上对驶。“翔富8”轮采取避让措施不当,违反《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
综合考虑三艘船舶在瞭望、安全航速以及采取避碰措施的情况,根据造成碰撞紧迫局面的过失是划分责任大小的主要标准、碰撞紧迫局面下是否适当采取避碰措施是认定责任大小的次要标准之原则,涉案三艘船舶对碰撞事故的发生互有过失,而以“翔富8”轮的过失为大,应负本次事故55%的责任,“恒晖15”轮的过失为次,应负本次事故30%的责任,“东方223”轮的过失再次,应负本次事故15%的责任。
船舶碰撞事故责任认定意义重大,不仅决定当事人的民事责任,经常还会决定当事人的行政甚至刑事责任。针对海事审判中遇到的主要碰撞情形,笔者根据避碰规则等规定,结合海事审判实践,对事故船的责任认定总结出一般的责任认定模型,希望对海事法官、海事律师以及海事行政部门有借鉴意义,开创海事审判新局面,实现海事审判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服务于国际海事中心建设。
[1]王利明:《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7-18页。
[2]《民法典》第一百八十条:“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民事义务的,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不可抗力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
[3]广州海事法院一审案号(2018)初352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案号(2019)粤民终2770号。
[4]广州海事法院一审案号(2017)粤72民初1002号,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案号(2018)粤民终2627号,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审查,案号(2020)最高法民申1775号。
[5]司玉琢、吴兆麟:《船舶碰撞法》,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
[13]蔡存强编著 《国际海上避碰规则释义》,人民交通出版社1995年版,第136页。
[15]蔡存强编著,《国际海上避碰规则释义》,人民交通出版社,1995年版,第154页。
[19]广州海事法院(2009)广海法初字第4、292号,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粤高法民四终字第86、87号,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提字第142号。
[20]广州海事法院(2012)广海法初字第301号、(2013)广海法初字第565号。
[24]广州海事法院(2017)粤72民初1013号。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
...